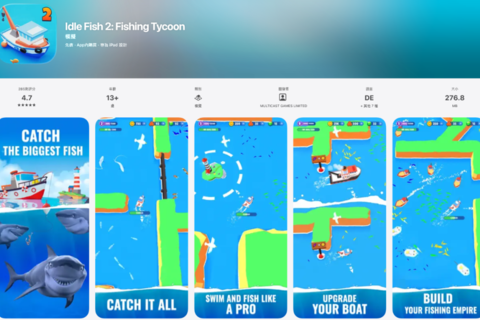你还记得淘金互动和他们的《地下城堡》系列吗?
2014年,该系列初代作品《地下城堡:炼金术师的魔幻之旅》上线App Store,凭借出色的文字描写和场景氛围,力压一众名作登顶iOS付费榜。
两年后,淘金互动趁热打铁推出续作《地下城堡2:黑暗觉醒》。基于前作的良好口碑,以及过硬的产品品质,该作上线第二天便冲上付费榜第一,苹果商店、TapTap等平台推荐位更是拿到手软。时至今日,《地下城堡2》仍是不少玩家心目中的白月光。
不过2021年的第三代作品:《地下城堡3:魂之诗》,却招致了一定争议。一方面,其上线首周便冲入畅销榜前5的表现有目共睹;但另一方面,一些老玩家却认为该作的商业策略略显激进,没了《地下城堡》系列“内味儿”。
如今又是四年过去,这个历时逾十年的国产经典IP终于在9月17日正式推出第4代作品,并拿下了多个应用商店榜单的第一名。
不久前,游戏陀螺与淘金互动发行子公司烛月游戏负责人林义耀及《地下城堡4》主策曹晨城聊了聊。我们聊到了《地下城堡》4做3D的原因,《地下城堡》中那些正在变化以及始终未变的游戏设计,也聊到了淘金互动为什么开始自研自发,以及PC市场快速发展对暗黑硬核类游戏的影响。如果你好奇于这个系列为何如此长青,那么你一定能从这篇对话中找到一些秘诀。
以下为对话内容,为方便阅读有所调整:
谈立项研发:从2D到3D,策划也得重新学习
陀螺:《堡4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?当时基于什么市场认知立的这个项?
曹晨城:2022年下半年就在构思了。当时《堡3》上线了一年多,《堡3》在制作当中,市面上有很多卡牌产品,因此《堡3》也受到了一定影响,有一些卡牌特性——量来得快,付费也快,但它的持久性相比《堡2》稍微差一些。所以我们开始酝酿《堡4》。
陀螺:刚立项《堡4》的时候,团队有多大?
曹晨城:立项阶段其实人很少,因为定了做3D,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,所以我们希望有更长的筹备期。最早主要就我跟制作人两个人去做一些核心结构的设计。此外还有服务端主程和客户端主程,他们形成一个小组,我们四个核心成员先逐步搭建Demo。到现在项目总共30多人,这其中也包括2代、3代的维护人员,像美术同学是三四个项目兼着做。
陀螺:团队里做《地堡》最久的小伙伴做了多长时间?
曹晨城:应该是《堡4》的制作人,他是1代策划,2代、3代、4代都是制作人。另外还有很多老同志,淘金10年老员工比例很高。
陀螺:《地堡》系列做到第四代,你们作为创作者会不会腻?
曹晨城:虽然都是《地堡》系列,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,像战斗、养成元素设计,包括玩法都是有变化的,并不是说我们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。我们每一款都是当做新游戏来做的,包括每一作的剧情也是相对独立的。
陀螺:除了产品的正常迭代之外,是什么促使你们每隔三四年就做一款新作?
曹晨城:因为每一代都会留下一些遗憾,而你会想做一款新作品去弥补遗憾。这就是研发的生命力所在。
陀螺:相比2代和3代,4代最大的突破是什么?
曹晨城:《堡4》主要是取了《堡2》和《堡3》的一些精华。《堡2》其实没做太多的商业化,纯粹是靠游戏性打出来的天下;而《堡3》则有意往商业化做了一些尝试。《堡4》把《地堡》系列的游戏性延续下来,同时又把《堡3》所积累的商业化融合进去,并用3D来实现。
陀螺:2D到3D,成本高了多少?
曹晨城:成本提高还是蛮多的,但更多体现在试错成本上。3D当然比2D贵,画张图和做模型成本完全不一样。但对于我们来说,立项时更担心的是我们能不能做好3D,选择方向是不是错了。不仅在于金钱成本,还有时间成本。
陀螺:那从2D到3D学习成本有多高?
曹晨城:对于我们这种过去一直做2D的团队来说,学习成本很难去量化,而且不仅是美术和程序,策划很多的设计放到3D下也不一样。
举个例子,我们之前的设计全是平面图,《堡4》我们想把地图做成接近于走格子的体验,但我们发现在3D的框架下做走格子的体验很不友好,因为3D所呈现的东西是具象化的,场景氛围没办法像2D那样做留白。它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,两头都不搭。最后我们尝试做了很多迭代,才做成现在这样。
陀螺:但我们看到很多团队现在不做3D,反而转头去做2D了。
曹晨城:我觉得应该从我们想表达给玩家的内容上去考量。
选3D的出发点很简单,《地堡》是一个偏暗黑西幻的题材,游戏体验代入感比较强,画面的提升肯定能帮助玩家提高代入感。《堡2》的剧情和表现更接近MUD游戏,《堡3》稍微加了一些美术表现,但还是以文字为主。而3D表现可以很直观地把策划设计的想法直观地呈现出来,塑造《地堡》的世界观。此外,从游戏开发角度来说,3D的配套设施已经比较成熟了,对于初学者也是值得尝试的。
陀螺:你们还用了真人动捕,贵吗?
曹晨城: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贵,这一块的配套设施已经相对成熟了,成本也比以前更低一些。
之所以用动捕,是因为以前所有动作都是我们美术人员手搓出来的。但是《地堡》的题材决定了我们的人物呈现必须是写实风格的,而玩家对细节捕捉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。经过反复尝试之后,我们发现无论怎么手搓,都搓不出动捕的感觉。所以最终决定整套做动捕。
陀螺:对产品要求更高之后,你们的整体成本控制得怎么样?
曹晨城:虽然《堡4》的开发成本相比《堡3》有提升,但算是控制在比较好的范围内,这些成本也主要是体现在3D建模素材方面。而在人员上,比如核心美术、核心程序从《堡2》和《堡3》延续过来的,他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研究3D技术,所以没有额外扩编太多的技术人员。
谈游戏设计:做竖版,给玩家最熟悉的体验方式
陀螺:《地堡》系列做到现在,有什么东西是始终没变的?
曹晨城:画风、文字剧情,策略性,这是四代产品都延续得比较好的三个点,只是表达形式不太一样。国内把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同类产品也确实不多。
陀螺:从1代到4代,《地堡》玩家最想要的是什么?
曹晨城:其实有时候玩家自己也说不清楚,他们只会给你反馈抽象化的东西。而我们作为开发团队,需要抽丝剥茧,落地到具体的游戏设计。
而从游戏设计角度来说,你很难界定玩家到底喜欢什么。有可能玩家喜欢的黑暗题材,有可能玩家喜欢的是这种玩法。整体来说,《地堡》相当于一个媒介,通过世界观、角色以及一些元素触达到玩家,跟他们建立情感。
陀螺:为什么做到4代了,你们仍然坚持做竖版?
曹晨城:原因其实很简单,最早做《堡1》选择竖版是因为希望玩家方便玩。
我们在做3D之前也讨论过要不要做成横版,因为大部分3D游戏横版表现会好很多。包括场景、UI、角色呈现,做成横版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
但我们的玩家从1代到现在这么多年,很多玩家之前是学生,现在慢慢成家立业了,他们只有一些零散的时间,这块体验竖版跟横版差别还是挺大的。最终我们认为,还是应该照顾玩家的感受,给他们带去比较熟悉的体验方式。
陀螺:现在节奏这么快,玩家还愿意花那么多时间看文字剧情吗?
曹晨城:这就是3D表现的优势所在了。比如描写一个战场、可怕的boss,我们不再需要大段大段的文字描写,只需要用一个3D场景就能很直观地呈现出那种感觉。
当然,文字有更大的想象空间,只不过在社会的变化过程中,大家不再有那么好的耐心去认真读每一个字。但我们仍然会保留文字部分,比如通过一些收藏品上的文字进行碎片化叙事,把《堡4》的世界观构建起来。
其实不单单是文字,包括游戏时间,我们也在尝试给玩家做减负。比如《堡4》的英雄是没有独立等级的,所有英雄可以同时升级,英雄招募也更加平滑。我们希望玩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们喜欢的内容体验上。
总的来说,《地堡》最核心的一些东西,我们要想办法以更好的方式呈现给他们;而某些东西,我们就要让玩家玩起来更便利一些。
陀螺:为什么做减负,是因为看到了放置挂机的行业趋势吗?
曹晨城:主要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设计倾向,我们不希望玩家为了某些资源投入过多精力。比如一些boss,玩家只要正常推进,是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就可以挑战的。哪怕你今天打不过,收两天菜过段时间也照样能打。当然,如果玩家有时间,他也可以慢慢钻研怎么打boss。
不过,我们本质上不是放置挂机游戏。《堡4》的核心依然是冒险、探索和剧情,而放置部分可以帮助玩家更好地推进游戏进度。
谈用户:《地堡》玩家,一群被遗忘的“老男孩”
陀螺:现在《地堡》系列有多少用户?
林义耀:到《堡3》为止是3000万的用户盘,其中《堡2》是全系列用户体量最大的产品。
陀螺:为什么2代的用户盘子能做到那么大?
林义耀:《堡2》上线于2016年。那时候不管苹果还是安卓渠道,对独立游戏支持力度都比较大,包括TapTap刚刚起步,渠道希望能给玩家提供优质内容。
所以《堡2》虽然推广宣发没花什么钱,但通过联运渠道的长期露出和资源曝光沉淀了大量用户。到2021年《堡3》上线,买量占比已经非常可观了,那时候大家都面临获客成本的问题。不过,虽然《堡3》用户盘子没《堡2》那么大,但整体结果也不差。
陀螺:《地堡》系列的用户画像大概是怎样的?
林义耀:整体来说,男性占比在95%以上。从年龄层来看,前3代积累的用户基本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为主。年轻用户也有,但他们的黏性相对来说没那么强。
所以我们的核心玩家叫“被遗忘的老男孩”,这类玩家有家庭,收入比较稳定,整体教育水平也较高。同时这批玩家游戏经历比较丰富,比较喜欢魂系或者偏硬核的游戏,主机玩家比例也不低。而且这些用户比较小众、垂直,和大众化的商业游戏相比盘子没那么大,愿意持续耕耘的厂商也不多,刚好《地堡》的风格契合这批用户的调性。
陀螺:之所以被遗忘,是因为这个群体很少主动发声?
林义耀:和二次元用户相比,我们用户确实相对内敛、沉默一些,他们更关心游戏好不好玩。但玩家也会自发地形成一些交流阵地,比如贴吧、Q群、微信。很有趣的一个点是,即便他们觉得你的游戏好玩,也不会明确说出来。但他们会花大量时间玩游戏、出攻略、写wiki。像前两代最长最完整的剧情大纲不是我们官方出的,而是玩家出于兴趣自发整理的。
但如果你的游戏不好玩,他们也会直言不讳地讲出来。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一个地方——这证明玩家对我们是有期待的。
谈发行及IP:信息大爆炸时代,买量已成“必选项”
陀螺:你们的用户主要集中在哪些社区和平台?
林义耀:TapTap是我们最核心的阵地之一,另外B站也是一个阵地。从我们调研的用户画像来看,B站用户和《地堡》用户非常接近。小黑盒也有,但它的触达方式没那么直接。
陀螺:你们会通过什么策略去撬动玩家?
林义耀:比如在预约阶段,会通过一些私域运营的手段,对老用户进行召回。之后还要通过一些渠道合作、买量,把用户盘子做大。
陀螺:《地堡》更像是一个靠口碑传播的产品,为什么你们还要去买量?
林义耀:这么多年做下来最宝贵的一定是《地堡》的核心玩家,但现在的市场环境下,买量是不得不做的事。酒香也怕巷子深,还是需要通过买量的方式去触达更多用户。
曹晨城:现在触达新用户的成本比以前高很多。如果不买量,不要说新玩家,老玩家可能都不知道《堡4》要上线了——这个时代信息太爆炸了。
陀螺:《地堡》这类产品,买量成本在市场中处于什么水平?
林义耀:以《堡3》为例,它的成本应该是同品类的正常水平,但跟SLG和卡牌相比就算低的了。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的买量盘子多大,游戏商业化深度能不能支撑。
虽然《地堡》系列有3000万用户,但这个品类跟其他一些主流游戏相比还是比较小众,盘子也不算特别大,基于我们现在团队的能力,把这个细分盘子运营好就很不错了。
陀螺:我看你们还拍了部短剧,是想通过这种新形式去触动老玩家吗?
林义耀:短剧其实不算特别新的形式,很多发行把短剧作为游戏宣发模式。对我们来说,为什么考虑做《地堡》短剧?初心是想给《地堡》玩家创造一些可以观看、讨论的内容。这部剧的出品人就是地下城堡系列全体玩家。我们认为,是因为有《地堡》玩家的支持,才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个产品做这么久,有机会拍一部玩家喜欢的短剧。
另外从宣发角度看,我认为短剧本身很难达到纯品宣的曝光效果,我们也很想看看短剧视频宣传的素材效果如何,能否对我们的投放起到帮助。
陀螺:为什么这次《堡4》会选择自发行?
林义耀:相比代理发行,自研自发有几个优势。
第一,离研发和玩家更近一些。一般来说,代理发行会在产品研发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介入。而对于自研自发团队来说,我们可以从立项到上线全程陪着研发。包括产品方向的沟通,品质的打磨,用户画像调研,去帮助研发做产品调优。
第二,从营收角度来说,自发行比代理发行的收益更大。
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点是,我们想去做《地堡》IP的运营。我们希望从《堡4》开始把《地堡》IP持续做拓展,去做延续和运营,这是最核心的点。
陀螺:到了这个阶段必须做IP化吗?
林义耀:至少我们觉得,《地堡》系列到了第4代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。比如把资源聚拢到研发侧,整体考虑IP的未来走向。长远来看,我觉得这是不得不做的选择,至于IP能够产生多大价值现在没法下定论。但我们会把这个系列产品持续做下去,这是肯定的。
陀螺:我看你们还做了一些周边?
林义耀:我们也有考虑做一些周边变现,但最开始的目的还是回馈给玩家,以活动的形式送给玩家,如果能够拿出来做一些商业化尝试,当然更好。
其实国内暗黑风格硬核玩家对手办的诉求很多,但这么多年下来《地下城堡》系列一直没有玩家认可的角色手办。我们4代会做这样的尝试,玩这类游戏的玩家机械键盘占比比较高,所以我们考虑做键帽,而且我们键帽也做了不同材质的划分,后续也计划以比较优惠的形式售卖给玩家。
谈市场:《黑神话》爆火,对暗黑硬核类产品是利好
陀螺:你们坚持做单机化游戏体验,是认为它有稳定的市场盘?
曹晨城:我觉得单机和网游没有太大的隔阂,只是游戏的一种体验方式而已。像黑魂系列的《艾尔登法环》加入了PVP和联机玩法,从体验上算是单机还是网游?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。
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单机,只是我们想做的冒险和剧情体验,用单机方式来呈现是很好的。如果未来某些玩法希望玩家用交互的方式去完成,可能我们也会去加这类设计。我觉得这不是限定团队设计的准则,核心还是好玩。
陀螺:现在用户接触的单机大作、多端产品越来越多,他们的审美阈值也越来越高,这对你们会有影响吗?
林义耀:现在很多厂商在做PC游戏,某种意义上也在培育和扶持这个市场,这个市场的空间必然会上涨。刚好《地堡》系列是西幻题材,它的受众在国内没那么多,而我们认为,暗黑魂系硬核类的产品,它的市场空间远不止《地堡》系列现有的3000万用户。
比如一部分玩《黑神话:悟空》的玩家,可能之前都不知道Steam,但因为《黑神话》爆火之后,更多人会去了解这个平台,了解《老头环》《黑魂》这些暗黑向的单机游戏。我们虽然是做商业化手游,但我觉得二者之间存在一定交集。
陀螺:但感觉移动端上,小而美不如前些年在渠道和发行受欢迎了?
林义耀:因为流量贵,需要花钱去买露出,LTV低获量就很难,所以逼着厂商去做一些商业化产品,没办法。除非你做主机类的产品。
从平台角度来说,迫于营收压力,他们从资源分配模式变成了算法模式,编辑给予的免费资源会逐步减少。所以对纯粹做独立游戏的团队来说,即便产品本身品质不错,但曝光不多,独立游戏的商业化空间也会相对有限。这是行业的大趋势。
陀螺:现在中国游戏行业,大厂鲸吞市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了,你们慌吗?
林义耀:担心肯定是有的,比如《龙息》上线的时候,我们也担心有冲击。但从开发角度来说,我们还是专注于做好自己。别人怎么样,你没办法控制,过多担心没有什么意义。
像《堡2》当年上线的时候,也有一些同类的模仿产品出现,但是很多产品都没有走到现在。我们认为游戏本身的一些核心设计是其他厂商未必能完全学到的。核心还是在于,一些大厂不一定看得上这个品类。那么我们就专注这个品类,做擅长的东西,至于外部因素我们没必要考虑太多。
陀螺:是什么让淘金互动穿越这么多个周期?
林义耀:一是坚持初心。另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不瞎折腾,团队一直保持比较小的规模。哪怕某一代产品营收规模更大,我们也不会盲目另开项目。特别是目前的市场环境下,如果一不小心失控,就会对公司运营产生很大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