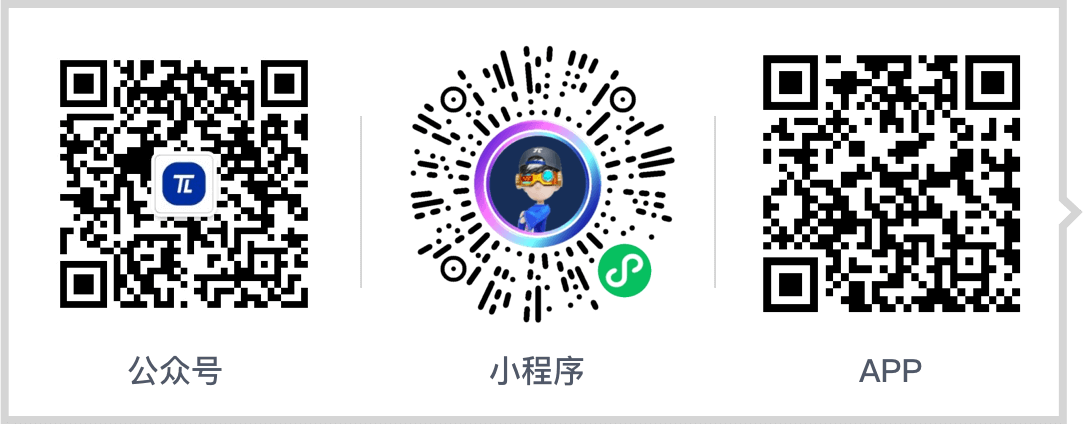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写过一本书,名叫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。这本书的观点和水平如何暂且不论,对于这个书名,我是不以为然的——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,绝大部分都没有侠客梦,只有“当官梦”,以及“国师梦”。
“国师”和“官”不是一回事吗?当官当到了极致、能够左右天下大势,就进入“国师”行列了吗?其实不是的。虽然“官”和“国师”有一定的重合之处,但无论在古代语境还是现代语境下,二者的区别都远远大于相同:
- 所谓“官”,是有编制、有俸禄的,需要通过考试(古代是科举,现代是考公或选调)。“官”要服从纪律,做许多日常杂事;绝大多数“官”的绝大多数时间是花费在繁琐的行政事务上的,对天下大势的走向并无影响力。
- 所谓“国师”,可以是“官”,也可以不是“官”。他们往往不需要通过考试,不是官僚体系的成员,所以也不需要服从纪律,更不需要浪费时间处理日常行政事务,只需要向最高决策层出主意就行了。
比如说,刘邦麾下的张良就更接近“国师”的角色:不带兵打仗、不参与行政管理,甚至没有实权职位,但是刘邦对他言听计从,堪称二十四史中的头号国师。萧何、王陵、周勃这些人是“官”,陈平既是“官”又是“国师”,唯独张良只担任“国师”。这个国师做的很有派头,待遇也十分丰厚,天下统一之后刘邦张口就是“自择齐三万户”(作为封地);张良怕别人嫉妒,只要了一万户。反观萧何贵为汉朝第一任相国,初始封地也才八千户,陈平更是只有五千户。
又比如说,康熙皇帝特别信任西方传教士,尤其是南怀仁、张诚、白晋等耶稣会传教士,不但蒙受厚遇,其奏折还可以通过内务府直接上达天听。传教士们经常进宫给康熙讲解数学、天文学乃至西方哲学课程,并且在《尼布楚条约》签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虽然他们往往有一些官衔(例如钦天监监正、太常寺卿等),但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官衔层面,具备一定的“国师”身份。康熙为什么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(他儿子雍正则全面禁教),显然离不开这些“国师”的面子。
不但普通读书人羡慕国师,朝廷里的大官也羡慕国师:正规官员想给皇帝出谋划策,要通过奏章或奏折的方式,辗转多个官僚部门,最终还不一定能送达御前,送达了也不一定被当回事。哪怕皇帝看到了、提起了重视,大概率也是大笔一挥,送交相关部门负责人(最典型的是六部),让他们先提出意见。相比之下,国师则拥有与皇帝一对一交流的管道,与皇帝培养私人感情,让自己的观点在第一时间变成大政方针。有人说国师是“白衣宰相”,其实大部分宰相其实就是个大管家,遵循先例、照此办理罢了,哪里有国师的尊荣和权柄?至于那极少数有决策权的宰相,事实上算是“宰相兼国师”,其决策权与其说是来自官职,不如说是来自国师身份。
到了现代,社会日趋复杂多元化,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道路多了起来。然而据我观察,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当“国师”,还是趋之若鹜甚至有执念的。资本市场上尤其多见!当年我在券商工作的时候,经常能看到首席经济学家、首席策略师们自称“海里有人”,“我说的话对海里有影响力”;有些基金经理也这么自称。有些人是吹牛,为自己脸上贴金,但更多的人是真心相信自己能影响到“海里”——哪怕一时半会做不到,也要以此为目标去努力、去奋斗!
就在最近两个星期,我至少看到了五篇关于“中国经济向何处去”的洋洋洒洒的国师级文章,其篇幅从两三千字到三四万字不等。之所以没有出现更长的,不是因为作者不想写长,而是因为微信公众号推文有长度限制,不得超过五万字(别问我怎么知道的)。这些文章颇为关注中国经济最近几年、尤其是最近几个季度出现的若干奇特现象,包括但不限于:
- 净出口(贸易顺差)占GDP的比重日益提升,无论在总量上还是比例上,均已远远超过德国、日本等传统的外向型经济体。
- M1(狭义货币供应量)居然同比下滑。我看到无数篇文章一致指出:“历史上没有一次大牛市是在M1下滑时发生的!”
- 国家并没有像“候任国师”们盼望的那样,推出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,这使得“候任国师”无不人人叹息。
公允地说,这些文章大多使用了比较严谨的理论框架,考虑了多层次的现实数据,绝非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“民间经济学家”可比。附带说一句,B站上有一些财经博主也自称“海里听得到我说话”(名字就不点了),言之凿凿地宣称什么大政方针是征询自己意见之后做出的。这就不仅仅是“国师病”了,而是妄想型精神病,需要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及时进行收治。如果任其发展下去,后果很难预料。
回到正题,为什么说“想当国师”是一种病呢?因为他们普遍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决策机制。这一点也正常,毕竟隔行如隔山,没混过体制内的人是不太可能了解的。国内的投资从业者,无论卖方还是买方,最关心的都是政策,一天到晚找各路“专家”打听最新的风吹草动——可是关心不代表了解。许多人听了无数次“海里专家路演”,读了无数份产业指导文件,对上面的决策流程的了解还是天真到可爱。正因为天真,所以以为自己写的文章(无论两千字短文还是三万字长文)能够真的发挥“国师”的作用。
其实用大脚趾想想都知道:不能。乐意当国师的人这么多,凭啥听你的?张良的例子离的太遥远了,咱们就用康熙和传教士的例子吧。康熙之所以高度重视传教士,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西方技术、西方知识,不仅能满足他的好奇心,还能立竿见影地产生实效。南怀仁得宠,是因为他会造炮、造机械,他造出的炮在三藩之乱中还发挥了作用;张诚、白晋得宠,是因为他们精通西方语言和国际局势,在与俄罗斯谈判过程中不可或缺。所有传教士还都具备高深的天文学知识,在相信“天人感应”的中国古代,这种知识的分量如何,不言自明。
简而言之,少年康熙出于对西方知识的好奇而接触传教士,出于西方科技的实用性而依赖传教士。就连征伐噶尔丹期间患上疟疾,都是通过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霜治好的。所以传教士附带对国家大事发表一点意见、为天主教传播争取一些资源,那都好说!除了皇帝本人,当时朝中的重要大臣,例如有“佟半朝”之称的佟国维、隆科多父子,跟传教士的关系同样十分良好。雍正元年宣布禁教之后,少数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仍然受到达官显贵的礼遇——毕竟当官的生了病需要西药,看风水需要西方历法,画个肖像也希望用西方透视法呢。
回过头来说,现在想当“国师”,动辄万字长文指点江山的人,根本不具备传教士的上述作用,因此很难得到决策层的认真阅读,更别说被吸收进决策流程之中了。头脑稍微清醒的人,理应认识到这一点,毕竟此乃常识。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拒绝相信上述常识呢?就连我的好朋友里面,也不乏发自内心认为自己可以当“国师”的,这让我颇为吃惊;我花了很大工夫才弄清他不是在开玩笑。
从坏的方面讲,当“国师”的诱惑太大了,谁不想像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之中、轻松得封万户侯?就算是不受身外之物的传教士,想给自己修个教堂或积累一批高端信众,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不过我相信人性不完全是恶的。很多人(譬如我的那位朋友)想当“国师”,根本原因还是有责任感,希望对历史进程发挥一点微小的作用。他们求回报吗?肯定是求的,但是他们想象的回报并非财富或权力,而是名垂青史的自豪感。
从这个角度讲,“国师病”堪称中年人(尤其是金融圈中年男性)的“中二病”。我们小学的时候总是希望成为动画片里的超人,中学的时候又希望成为武侠小说里的大侠;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“中二病 ”不治自愈了。可是大家总归对自己的“历史地位”存在盼望,对自己的“历史影响力”有幻觉。一言以蔽之:未成年人的中二病是“我很特殊”,成年人的中二病则是“我很有影响力”。国师病只是成年人中二病的一种常见体现罢了。
因此我觉得,跟我们小时候的“中二病”一样,“国师病”也不一定需要治。有这个病的人,往往是责任感过剩的,我们总不能说有责任感是坏事;没有这个病的人,往往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过度现实,对人类毫无真正的帮助可言。我希望这样的“候任国师”不要消失,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总归是好的。
当然,那些在B站、抖音上面通过“民间经济学理论”乃至“阴谋论”自称国师的创作者是毫无价值的。我希望他们的数量少一些并且永远不要引发真正的影响力,尽管我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——就像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一个人在大街上说傻话、自称世界首富并欢迎大家拍照。至于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傻话,则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了。